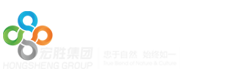
香港富商陳啟宗繼以家族慈善基金“晨興基金會”名義向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捐贈3.5億美元(約21.5億人民幣),這一哈佛378年校史上金額最大的單筆捐贈后,9月18日,陳啟宗與夫人再向南加州大學職能科學與職能治療學部捐贈2000萬美元,這是一周內“晨興基金會”向美國大學提供的第二筆善款。
近日,陳氏家族的捐贈行為在網上引起了廣泛討論,為何中國的企業家不捐贈中國的高校,卻要捐錢給國外高校?
中國企業家向國外高校的捐贈行為確實不是個案。2010年1月,中國人民大學本科畢業生張磊,向耶魯大學捐款8888888美元,用于管理學院新校區建設,成為耶魯管理學院畢業生(張磊為耶魯大學MBA)捐贈的最大一筆個人捐款。2011年1月,中國溫斯頓電池制造有限公司創辦人、稀土鋰電池發明人鐘馨稼向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捐贈1000萬美元,資助該校伯恩斯工程學院開發清潔電池、太陽能以及可持續交通研究,成為該校有史以來最大的一筆個人捐款。 2014年7月,SOHO中國董事長潘石屹向哈佛大學捐款1500萬美元(約9300萬人民幣)成立“SOHO中國助學金”。。。。。。
其實,企業家的捐贈意愿本屬個人行為,我們無權妄加評論或干涉,但是捐贈行為的背后映射出的中國公益事業的問題確是我們想要去探究的——中國的公益慈善到底出了什么問題,使得中國企業家的捐贈款紛紛“外流”?
中國企業家的尷尬
現年65歲的陳啟宗曾在接受記者訪問時指出:“在內地行善,有時會自討麻煩。”他回顧當年捐助故宮修復建福宮的事,但后來被爆出的“會所門”事件搞到心寒。而對于他口中那些自討麻煩的項目細節,陳啟宗不愿談及。他指出,內地學術腐敗以及學術風氣有待改善,“學術不嚴謹,做不出世界一流的研究,”這也是他捐助哈佛的部分原因。
許多中國企業家都曾表示,他們所在的企業曾經與中國高校合作過,包括聯合開展研究、設立聯合實驗室、設立獎學金等等。但是,這些事項后來都慢慢停止或縮減,其中原因主要體現在項目缺少監測和跟蹤、科研進展緩慢、科研成果難以與企業需求接軌,甚至還有項目資金挪用等等問題。
中國企業家以捐贈報效國家的一番熱忱被一次次打擊。
中國教育慈善事業的窘迫
國外的大學,有專業機構負責募捐,社會募捐的經費是保證學校獨立辦學的重要力量,學校在給捐贈者冠名、使用捐贈資金等方面,有規范的制度,包括通過學校理事會決策、廣泛聽取師生意見,在學校治理過程中,實行學術自治、教授治校,捐贈者并不能干涉學校的辦學等等。
在這種現代大學制度之下,學校辦學信息公開、辦學經費都必須用于教育教學和學術研究,因此,捐贈者并不擔心捐贈的資金會被濫用。可我國內地高校則不然,由于缺乏現代大學制度,近年來就連國家撥付的經費都存在被揮霍、鋪張浪費,甚至貪污的情況,因此,很多捐贈者對捐贈內地大學,要么處于觀望狀態,要么被捐贈后無下文的結果逼退。
在公益慈善相對成熟的社會里,公益組織應對捐款人承擔的責任包括:所有的善款用于幫助實現基金會的使命、獲得適當的表揚與認可、獲得基金會的審計報告、工作報告以及對捐款人隱私信息的保密等等承諾。而這一系列制度性的保障,反觀國內高校,國內大學的基金會依然難以實現,究其表面原因是國內大學基金會缺乏專業化的管理制度,深層原因是國內大學基金會的理事會大多由大學現任行政領導擔任,是大學行政體系的附庸。所以,國內大學基金會如何讓自己轉變為一個教育類慈善公益組織至關重要。
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浙江馥莉慈善基金會嘗試“有效公益”
從2012年至今,宗馥莉已經先后對國內兩所高校進行了捐贈,金額達到一億七千萬。關注慈善,其實僅僅是宗馥莉整個事業版圖的一個部分,她更大的夢想,是希望能為中國整個食品行業產業鏈的完善做出努力。
2012年,她捐資7000萬元與浙江大學合作設立馥莉食品研究院。這是一筆數額相當巨大的高校捐贈,用于中國特色食源開發和食品營養與安全的科學研究,側重食品的基礎研究。對宗馥莉女士及馥莉慈善基金會來說,捐贈高校開展食品領域的科學研究,不僅是事關中國食品科學研究領域的事,更是事關中國食品領域人才發掘與培養的大事。
當然她也知道,要解決全行業的生態問題,僅僅規范前端產品研發階段是遠遠不夠的。“我是整個生產的過程都要去管,不能只管了最原始的一部分,這樣我才有可能把整個行業慢慢地撐起來。”
因而在2014年5月,宗馥莉又捐資一個億,與西安交通大學合作成立馥莉食品科學與工程學院。這是一個全新的教育項目,針對中段食品生產過程,專項培養食品機械領域的高級工程師人才和行業領軍人才。三年間,做出如此大的兩個舉動,她在高校的選擇上,著實費了一番功夫。
“我們從來都是主動出發尋找項目的,雖然這樣要比被動接受項目耗費的精力更大、時間更長、磋商更久,但只有這樣我才能確保受贈方的質量,保證理念的一致。”
選擇捐贈的高校時,馥莉慈善基金會不僅將學校的科研能力、教學質量、高校排名等因素作為選擇的標準,更重要的是學校及校領導的教育理念與公益理念是否與馥莉慈善基金會一致,這是馥莉慈善基金會選擇捐贈對象最重要的一條原則。為了這一原則,宗馥莉或帶著工作人員跑遍全國拜訪高校,或邀請高校來杭協商,對于捐贈對象的選擇,最短的也歷時半年之久。
自從“郭美美事件”以來,中國慈善業的弊端就被放置在顯微鏡下。在大的慈善環境不完善時,宗馥莉跟很多慈善家不同,她不敢掉以輕心:她會以項目制的方式去考核團隊和基金善款的執行情況,親自參與學院師資的聘請、課程的設置、研究目標和方向等工作中......這便是外界所傳的最“嚴苛”慈善家的由來。
之所以特別重視教育理念的吻合,是因為馥莉慈善基金會對自身所秉承的公益理念的堅持:不想把教育公益做成“撒手掌柜”般的慈善事業,而是要在不干涉學校教學工作的根本原則下,監督受贈者對捐贈項目各工作的開展,推動“有效公益”機制的建立。
包括以嚴格的合作條款明確強調捐贈款項的使用范圍,并在每學年度結束后針對款項使用做檢查,力求款項使用到位發揮作用;邀請高校校長、書記與學院領導及捐贈者共同組成理事會,更好的為學院的發展把握方向,實現公益目標;請學院定期反饋工作內容,以對學院各項建設工作做到更好的了解等等。這些在馥莉慈善基金會看來,都是作為捐贈者的職責與受捐者的義務。此外,馥莉慈善基金會還認為受捐者應擔負一定的社會責任義務。作為科研院所,不僅要將研究院的教學與科研做好,更要將研究院的優秀成果與最新成績向社會公開,履行好研究院作為科研院所的責任。
“有效公益”是宗馥莉的大膽嘗試與創新,她堅信,我們這一代人需要去做這樣一個事情。馥莉慈善基金會一直在中國的教育公益領域中做著嘗試,試圖探索一條中國企業家捐贈教育等公益事業的可行之路。
關注“有效公益”的首個項目: 浙江大學馥莉食品研究院
浙江大學馥莉食品研究院是馥莉慈善基金會嘗試“有效公益”的首個項目。據基金會的工作人員透露,基金會從反復協商捐贈條款開始,就為該筆捐贈制定了包括按需撥付年度款項、為科研制定成果指標、每年強化學院工作考核等等一系列舉措。
今年夏天,浙江大學馥莉食品研究院將第一批參與國際交流的10余名學生送出國門,同時迎來了第三屆新生。在兩年的時間里,研究院取得了令業界關注的優異成績:
他們嘗試并成功在國內教學中實踐了IFT教學理念和標準,通過積極引進國外名師全英文教學,采取小組討論(Workshop)、課程設計(Project)、課程實踐(Seminar)和學生報告(Presentation)等國際化的教學和考核模式,為國內高校教學模式的改革作了有益借鑒; 他們鼓勵學生以自主尋找課題開展研究的方式取代傳統的跟隨導師被動性參與研究的方式,學生們針對“食品安全與營養信息的網絡搜尋和甄別”、“粵式飲食的特點和科學”、“中國飲食變化與慢性疾病的關系”、“家庭飲食習慣變遷”等等議題做了調研并發布調研報告,調研報告獲得達科他州立大學Kalidas Shetty教授的充分肯定,并特意向研究院發來郵件邀請研究院學生到美國深造;2013年11月,由浙江大學馥莉食品研究院主持進行的浙江大學中國特色資源植物化學素數據庫項目建成。在研究院整理獲得的第一批近4900多條關于楊梅、柑橘、竹、梅、荷、食用花卉、茶、香料、漿果等植物化學素的國內外研究文獻數據,已有700條數據被上傳,并被數據庫錄取400條;兩年中,共授權發明專利13項、發表SCI論文25篇、開展國家級科研項目7項、省級科研項目5項.....
浙江大學馥莉食品研究院執行院長劉東紅曾這樣表示:“兩年以來,全國的同行對我們的人才培養實踐都給予了高度的肯定,也得到了國際上同行、學生、學生家長的認同;研究院發表的研究文章不斷增加,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基金的研究項目中、甚至我們研究院基金項目在基礎科學上的研究也得到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領導和專家們的贊許;我們的公眾開放實驗室已經拍攝了十多期的節目,很好的向社會公眾傳遞食品安全與營養知識。尤其重要的是,在公眾科普活動的參與過程中,學生們逐漸增強了社會責任感。”
中國公益慈善的道路該如何長久的走下去,還需要各行各業、各領域及政府專家的探索,但固步自封,明知存在的問題卻無法沖破思維去解決是堅決不行的。中國公益慈善事業,是時候戳戳你的脊梁骨給你點提醒了。